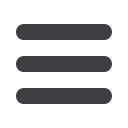

102
103
今年四月底時,我們首次前往來義,跟部落內一位傳唱古謠的
vuvuSa
’
enge
學
了第一首歌
atapitjusaliljing
;在傳唱與轉述的過程裡,
vuvu
的思緒與目光已不在我
們所處的當下,歌謠將她拉回遙遠⋯她在舊部落家裡的味道,與情人夜晚濃濃的情
愫。她右手托著腮手指不斷地在下眼瞼處摩擦,我沒多留意這舉動,
vuvu
是性情中
人,她是想抑制自己的眼淚,但情緒滿溢還是悄悄流了下來。她說她很想念,想念
舊部落、想念父母親、想念自己的童年、也想念自己的舊情人。年輕人很難想像到
底是有怎樣的感覺,讓他們輕易的就神遊在自己的想念裡!排灣族的神話與歌謠有
內隱的抑鬱,但不是憂鬱⋯是一種愁思,對人、對事、乃至大自然。他們似乎不太
著迷於歷久不衰的美,一閃即逝的永恆⋯常存
在他們心裡,他們說這樣的美是
samiling
!
是超越美這樣世俗的字眼,是神話傳說裡才會
出現的奇觀!我們一句一句的溯著歌謠,希望
能順著煙⋯慢慢走進歌謠的生命裡。然後,感
謝祖靈。我們的成果刊物真的出來了。這是最
最困難的一件事⋯除了讓我們感到緊張更是
興奮。耆老們的文化記憶太溫暖、太豐厚了,
不該只是留在我們後代哀嘆的愁思之中。那樣
太浪費了。
朱克遠
/TAI
身體劇場藝術行政
許培根
/TAI
身體劇場一般行政
王 傑
/
大漢技術學院觀光系學生
徐智文
/
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
潘志宏
/
花蓮縣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文創人員
賴恩柔
/
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舞者
陳文潔
/
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學生
團隊成員
成 果 分 享
行腳部落,探訪家名拜訪族人,繪製部落地圖
大學畢業後,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工作了一段時間
;
也許是因為大學所學,在學習表演的過
程中,老師不斷的提醒我們認識自己的重要性,而我也漸漸察覺到自己對於原住民身份的排
斥。在一次的機會,找到是劇場相關工作,又是跟原住民文化相關,毅然決然就接下了工作來
到花蓮。之後就一直待在花蓮從事劇場工作,同時學習自己及其他原住民族群的文化。在來義
曲文化傳習班的這段期間,一開始並不是很順利,參加的青年們雖然很多,但似乎都不太主
動,歌唱不大聲、舞也跳不起勁,課程時間,也有時候來,有時候沒來。而我就我自身的經驗,
我知道也許文化認同,每個人有個人的時間,我們的迫切,對這些青年來說,也許是一種干擾。
但在一次跟部落同樣也參與工作坊的部落姐姐們聊天之後才發現,這些有些是她們孩子的弟弟
妹妹們,在家的時候,已經開始喜歡聽、喜歡唱那些我們所教的歌,唱的這些姐姐都有點煩了,
甚至還急著想學那些我們還沒教的歌。原來工作坊時的不主動,只是一種害羞表現。在部落收
獲節的那一天,我們讓這些弟弟妹妹小朋友們,在老人家面前表演所學的歌曲。看到他們大
聲驕傲唱著自己的歌,我高興的同時,也提醒自己,他們追上我了,他們已經會唱自己部落
的歌了,而我還在唱別人族群、別人部落的歌,我也要加油,回自己的部落,學自己部落的歌。
最 感 動 的 事
傳習班每天行腳部落,
手繪出具部落情感,與
土地溫度的部落地圖
部落收穫祭時耆老們圍坐在
舞圈中央,開心的看著青年
及孩童們傳唱、舞跳著古謠

















